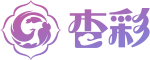不稳定的工作,对人的伤害有多大?
日期:2025-11-20 21:28:36 / 人气:68

随着时代的变迁,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在近几十年来发生了哪些转变?我们该如何去理解、去看待这个世界,该如何体验生活和世界,才能免于被抑郁症等精神疾病纠缠?
《疲于做自己:抑郁症与社会》首版于1998年,早已有英语、德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等十来个译本,书中内容不断被各国学者研究、评论、引用。随着抑郁症越来越成为流行病,这本书焕发出令人震惊的生命力,从而确立了其社会学经典著作的地位。
抑郁症不仅体现了人们想做自己的激情和成为自己的困难,还展现了社会对个人主动性的要求和个人满足这个要求的困难。
如何很好地行动起来?每个人都被敦促通过调动自己的心理能量而非借助外在规则去实现这点。
(以下为正文)
对于抑郁症患者而言,目前科学承诺的前景依然停留在魔法层面。在评估这些神奇承诺是否真实之前,我们需要看到,这些承诺回应的是一种社会期待,它用新语言将当今人们面临的问题表述了出来。首先,社会对痛苦的重新关注凸显了经济遭遇危机的社会病态,危机造成的创伤和压力以抑郁症的形式在精神病领域表现了出来。其次,行动方面的个人化进程导致个人性必须承受新的压力,个人必须不断接受这个现实,适应这种压力。
痛苦浪潮
在20 世纪 80 年代初至 90 年代,根据经济和健康研究、学习与文献中心(CREDES)的数据,法国抑郁症的发病率上升了 50%。虽然数据上涨的部分原因是现在人们更容易承认自己得了抑郁症,但“抑郁症发病率的上升是必然的。……抑郁症的发病率随着人们所处不利境况的增多——孤独、低收入、失业——而增加”。粗略地说,既定时刻测量的抑郁者的比例从约 3%上升到了接近5%(其他研究估计的数值是6%或7%)。欧洲国家之间的对比研究数量稀少,但结果都显示出了难以解释的明显的统计差异。
此外,抑郁症还伴随着自杀、酗酒、吸毒和一系列非精神类疾病。在同年龄组中,抑郁症患者自述的疾病比非抑郁症患者多得多(7∶3):有健康问题的20—29 岁的抑郁症患者所占的比例与45—59 岁有健康问题的非抑郁症患者所占的比例一样多。年龄在 45—59 岁之间的抑郁女性的健康水平相当于 80 岁以上的老人。因此,研究者写道:“抑郁症患者可谓未老先衰。”他们患上消化系统、泌尿生殖系统和心血管疾病的概率是普通人的三倍,患上癌症以及内分泌、骨关节等疾病的概率是普通人的两倍。他们消费的药物量(包括非精神类药物)和就诊次数都远远高于普通人群。直接损失(就诊、治疗等)和间接成本(缺勤、生产率低下等)看起来都很严重。抑郁症似乎处于一个非常多元的病情局势的中心点。
分析表明,抑郁症是许多病态心理问题的共同症状:酗酒、暴力、毒瘾和自杀。心理病理学家通常把吸毒和暴力解释为人对边缘型抑郁采取的防御。1997年,第二次全国健康大会的报告强调,青少年健康教育应该纳入“对诸如暴力和抑郁等心理与社会行为”的解释以及对攻击他人和自我攻击行为的解释。“筛查苦闷造成的疾病障碍应该成为优先事务。”学术研讨会的结论和官方报告还强调,在贫困、不稳定和存在社会排挤的环境中,应该注意多重压力交织给人带来的伤害,暴力、抑郁、心身疾病和多重创伤层出不穷。
今天,所有相关的精神病学报告都认为,有必要“将一些非精神疾病引发的痛苦也纳入考察范围,尽管这些痛苦不一定会导致疾病,但会致使当事人求助医疗系统”。
今天,精神病医生的职业已经不再以精神病为中心,而是面对着各种社会问题和心理疾病复杂交织的局面,医生必须考虑它们之间联系,同时做到仔细甄别——只要精神病学没被简化成社工工作,这种努力就是必需的。抑郁症揭露了(或者说是联结了)多种社会问题和医学问题。这些问题给我们的社会,尤其是对我们的社会保障系统,造成了高昂的成本。
法国总体规划委员会意识到“处于就业年龄人群的脆弱性增加……这是一个全新的现象”。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经济危机似乎已经在35—44 岁年龄组中导致了自杀人数翻一番的结果。孤独增强了这种脆弱性。工作场所的心理咨询诊室接待着“尽管还在工作,却因担心失去工作而寻求心理帮助的人”。按照法国公共卫生部门的说法,“在健康领域,精神痛苦显著已经成为最常见的脆弱症状”。
越来越多没有精神病但在遭受痛苦的人开始向公共精神病学求助。现在,不稳定的生活条件对人造成的创伤已经成为精神科医生治疗最多的问题:抑郁症、慢性焦虑症、毒瘾、酗酒、长期的自我用药——精神病患者的比例在绝对数量上保持了稳定,但相对比例却在下降:“失去希望正在成为主要危险。”抑郁症(而非焦虑或恐慌)处于多种创伤疾病和成瘾问题的交叉点。它有将一切串联的特性。这种对痛苦的关注以及用抑郁症来理解和定义社会问题的做法,是最近才出现的。
行动的个体化
如今,行动变得个体化。没有别人会代替你行动,人只能自己对自己的行动负责。于是,个人能动性成为衡量一个人价值的首要标准。
20 世纪 80 年代初以来,法国发生了两个具有象征意义的事件:一是左派上台,但它的(让左派能够证明自己是左派的)公共计划遭遇了失败;二是企业家的行为模式被视作所有人应该遵从的行动典范。两个事件彼此联系,导致作为左派进步理念核心的改良主义和革命这两大乌托邦同时衰落:它们本应创造确定的社会,是资本主义的替代方案。
企业家的形象从支配小人物的巨头或唯利是图的“地主”转换为拥有良好行动力的楷模,代表着每个人都应该使用的行动模式。事实上,企业家式行动模型是对国家行动陷入泥潭的一种回应,按照法国的传统,本应是国家肩负起社会的未来。企业家的形象成为激发整个社会政治活力的参照系。对于像法国这样的国家而言,这是一个明显转变:私人行为接管了国家的集体使命,公共行为也重新采用了私人模式。国家这个“公民的”公司必须将企业运作方式同行政管理职能结合起来。
赢家、运动员、冒险家和其他斗士形象开始占据法国人的想象。比如,今天,这样的形象体现在了一个尽管落魄却象征着法国社会进入竞争文化的人物身上:他就是伯纳德·塔皮。大家还记得吗?他是1986年法国电视一台黄金时段的一档创业综艺节目的主持人,这个节目有一个霸气的名字,叫“雄心勃勃”。它可不是一档简单的脱口秀。它倡导的第一波解放潮流是号召每个人都从征服自己的个人身份做起,它掀起的第二波解放潮流是宣扬个人凭借个体能动性去获得社会成功。
在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里,纪律模式(泰勒式和福特式)正在被激励员工自主行为的新规范取代,即便是最底层的员工也被囊括。参与式管理法、谈话小组、人才圈等,这些管理技术都以向每位员工灌输企业精神为目的。管理和支配劳动力的方式已经不再依赖机械的服从,而是强调人的主动性:责任感、发展能力、制订计划的能力、干劲、灵活性等,这些名词得到了新的管理方式的推崇。施加在工人身上的约束,其目的不再是把他变为重复劳动下的机械人,而是让他成为懂得灵活工作的自我管理者。人力资源工程师弗雷德里克·温斯洛·泰勒曾在20 世纪初把培养顺从员工、将人变成“任劳任怨的牛”(这是他的用词)作为管理目标。
今天的人力资源工程师们致力于培养人的自主性。管理的重点不再是驯服身体,而是要调动每个员工的情感和精神力。因此,今天我们面临的约束问题和定义问题也跟着发生了变化:20世纪 80 年代末以来,据入驻工作场所的医生和企业社会学研究员们的观察,新的焦虑情况、心身疾病和抑郁状态渐渐变多。企业可谓生产神经性抑郁症的门厅。
在 20 世纪 80 年代,人们对工作的投入度有所提高,但他们获得的稳定保障却在80年代末显著减少:首先受影响的是非熟练工人,然后是更高阶层的人,到了20世纪90年代,不稳定性直接影响到了公司高管。人们的职业生涯变得越来越不稳定。不平等的方式也在发生改变,这对集体心理产生了影响:在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不平等之上,又增加了群体内部的不平等。具有同等学历和相同社会出身的人,在获得成功上所面临的不平等在加剧。这种状况只会加重人们的挫折感,让他们的自尊心更加受损,因为人们看到,爬到他们头上的不再是一个遥远且不认识的人,而是自己的邻居。个人的价值感在这类不平等面前更加脆弱。
学校经历的变革也对学生们的心理产生了类似影响。20 世纪 60 年代,大多数时候,社会选拔发生在学业要结束的时候。然而今天的教育社会学研究一致显示,随着高中教育的普及,这种选拔贯穿了整个学校课程。与此同时,“人们对个人成功和学业成功的要求加剧,这些又都统统落到了儿童和未成年人身上”。一方面,学生承受的压力越来越大;另一方面,学生还必须为自己的失败承担一切责任。这种情形必然导致各种形式的自我耻辱感。这里,同样体现了不平等方式的变化。
从 20 世纪 60 年代起,本应由家庭承担的社会化职能开始大规模转移到学校身上。在心理学的大力鼓励下(斯波克博士、劳伦斯·佩诺德等),儿童的自我发展成了父母最重要的使命。临床医生已经注意到,在这一时期出生的病人,其自我认同的基础非常薄弱。这是“人们在行使家长职责时过度情感化养育的”结果。而且,伴侣和家庭成员在“分离”过程中体现出的自主性也经常模糊了一方与另一方之间的象征位置,从而产生新的不稳定性。性别关系和代际关系的平等化导致关系的普遍契约化和永恒的权力斗争之间形成了张力。随着等级界限被消除,曾经常常与之混淆的符号差异也消失了。
无论在哪个领域(企业、学校、家庭),世界的规则都已改变。现在社会强调的不再是服从、守纪、符合道德,而是灵活、变化、反应敏捷等。自我控制、心理和情感上的灵活性、行动力:每个人都被要求去适应世界,这个已经失去稳定性和连续性的世界。这是一个充满暂时性的不稳定世界,它由参差不齐的流体进程和轨迹组成。这种制度上的变革让人觉得,每个人,哪怕是最卑微、最脆弱的人,都必须自己完成选择一切、决定一切的任务。
长久以来,变革都被认为是可取的,因为它关系到进步的前景,而且进步就应永不停止,社会保护也应不断扩大。如今,人们对变革的看法变得矛盾,因为下坠的恐惧和无法摆脱下坠趋势的担忧已经超过了人们对实现社会向上流动所抱的希望。人们开始倾向于诉说变革的危险,用“脆弱性”“不稳定”和“朝不保夕”等词来描述变革。一切都在变化,这是当然,但人们没有感觉到进步。再加上社会环境步步诱导人们去关注自己的内心,因此,“变化的文明”大大刺激了人们去关注精神痛苦。精神痛苦变得随处可见,并被囊括到追求内心平衡的多重市场中。
如今,大部分的社会张力都是通过“内爆”“抑郁崩溃”或具有异曲同工之妙的“向外爆发”(暴力、愤怒或某个感觉的爆炸)等词来表达的。当代精神病学告诉我们,个人的无力感可以凝结为抑制,可以在冲动中爆发,还可以导致强迫,让人无休止地进行行为重复。所以,抑郁症也是社会规范的交会处,这些规范包括界定行动的新准则、广泛使用“痛苦”和“不幸”的概念来看待社会问题的做法,以及药物研究和制药工业对此做出的新回应。
"
作者:杏彩娱乐
新闻资讯 News
- 热闹不再:酒店年会的消亡与职场...01-26
- 爱优腾新规之下,2026年网络故事...01-26
- 刘太格:中国城市做不好规划,是...01-26
- 逛沃尔玛:传统大卖场的现状观察...01-26